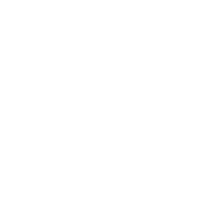发现存在的无意识: 罗洛·梅遇到奥托·兰克(三)
作者:罗伯特·克雷默(Robert Kramer) 中文译者:张文娟
(注:该论文公开发表得到了作者本人的同意,这也是该论文的中文版在中国大陆首次公开发表。)
“成为自己的勇气”或者存在的勇气?
1953年,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梅出版了《人类寻找自我》,随着流行音乐的歌词、病人的梦境,以及埃斯库罗斯、奥登、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菲茨杰拉德、歌德、卡夫卡、克尔凯郭尔、尼采、叔本华和华兹华斯的沉思之作,他在文本中翩翩起舞。梅的这本诗书完美契合了战后美国普遍存在的疏离感和孤独感,立即成为畅销书。用一个词——“空虚”——来捕捉1950年代冷战时期美国的情感基调,梅观察到“许多人不仅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常常不清楚自己的感受”(第184页)。
《人类对自己的探索》与他的朋友保罗·蒂利希的《成为自己的勇气》出版于同一时期,该书后来被纽约公共图书馆选为“世纪书籍”之一。艾布扎格写道,比起蒂利希那本植根于这位神学家路德教思想的厚厚的书,梅对灵魂的考古学用宝石般的、非宗教的语言表达了“成为自己的勇气”,“完全做自己的勇气,面对死亡的真相和生命中有限的细节,并允许爱和拥抱他人的潜力”(第186页)。
在他的个人生活中,仍与弗洛伦斯结婚的梅,最近与联合神学院教授大卫·罗伯茨(David Roberts)的妻子埃莉·罗伯茨(Ellie Roberts)开始了一段火热的恋情,罗伯茨和罗洛一样,是蒂利希的protégé会员。罗伯茨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神学家,是罗洛的同事和朋友。在《联合神学院季刊》(Union Seminary Quarterly)的一篇评论中,大卫·罗伯茨(David Roberts)称赞《人类对自己的探索》的抒情风格和“文学、神学、哲学、精神分析和临床趣闻的结合”(第189页)。1954年,44岁的罗伯茨自杀身亡,部分原因可能是罗洛与他的妻子(也是他三个孩子的母亲)的婚外情。艾布扎格不无遗憾地评论道:“谁能说得出,自杀所带来的不可避免却又被压抑的罪恶感如何影响了罗洛的良心和意识?”(第192页)。
“存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新维度
1958年,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梅与著名心理学家欧内斯特·安吉尔和亨利·埃伦伯格共同创作了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这本书引领了美国新一代心理学家如何理解治疗疗法的革命:《存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新维度》。引人注目的是,梅的序言和两章导言阐明了对存在主义哲学的欣赏如何成为所有心理治疗师——无论是精神分析学家还是行为学家——理解人类普遍的痛苦和孤独的核心。梅(1958)提出,通过创造性和同情心地关注存在的原始焦虑——原始焦虑——即从出生的创伤开始构成人类的存在,所有的心理治疗流派都可能被整合在一个单一的框架下,从而“产生对处于危机中的人类所有情况下的现实的理解”(第7页)。梅对心理治疗未来的令人惊叹的“整合”愿景,夹杂在其他撰稿人的错综复杂的散文中,被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和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等著名人文主义心理学家誉为一种揭示,他们迅速加入罗洛的行列,在心理学领域掀起了一股“第三势力”的风潮,超越了弗洛伊德和行为主义者的决定论,但保留了两者都有价值的东西。“存在主义-人文主义”(詹姆斯·布根特创造的一个组合)这个词第一次被同时使用,为治疗开辟了新的视野。
然而,即使在《存在》受到公众的赞美之后,罗洛仍然被“奴役他人真实和想象中的期望以及长期的不足感的折磨”所困扰(艾布扎格,2021,第220页)。罗洛拼命挣扎着寻找他的导师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所倡导的“成为自己的勇气”,“继续在非常富有成效的职业生活和焦虑、自我怀疑、嫉妒以及担心自己永远无法按照内心深处的冲动和信念行事的感觉之间徘徊”(第221页)。
52岁时,罗洛开始了另一段恋情,这一次的对象是26岁聪明、美丽、放荡的心理学家玛格达·丹尼斯(Magda Denes)。在这段新关系的起起伏伏中,罗洛很快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他在日记中写道,滑冰是“精神错乱的边缘”(第230页)。他和弗洛伦斯的婚姻长期以来在相互指责中处于崩溃的边缘,而弗洛伦斯也在追求自己的不忠。1967年11月,弗洛伦斯服用过量安眠药,企图自杀,两年后罗洛60岁时,这对不幸的夫妇最终离婚。
“爱和意志”
1969年,也就是他婚姻结束的那一年,梅出版了畅销书《爱与意志》(Love and Will),而此时正值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领导的美国,因为在越南打了一场血腥的、失败的战争而正在分崩离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历史学家,艾布扎格在展示梅是如何再次完美地捕捉到美国暴力的时代精神的最“恶魔”——《爱与意志》中最能引起共鸣的一个词。艾布扎格将梅的“现代悲叹”浓缩成两句唤起共鸣的句子,写道:“深厚的爱被翻译成了性的最低公共性。意志的力量已经被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个人无力感削弱了”(第267页)。
引人注目的是,罗洛在《爱与意志》中回到了奥托·兰克对“生命的真正春天”的隐喻(兰克,1936a, 289页),这一隐喻在30年前梅在他第二本书的标题中使用过。他在新书中声称,他的目标是“寻找爱和意志的源泉…… 正如法国人所说的河流的‘源头’——水最初来自的泉源。”他打算“寻找爱和意志的源泉,[为了]发现这些基本体验需要的新形式,以便在我们正在进入的新时代中变得可行”(1969年5月,第16页)。
在他的文章中,梅用与兰克相呼应的语言框定了爱与意志:“人类的任务是将爱与意志结合起来…… 我们有一种记忆,一种柏拉图意义上的“回忆”,在我们吮吸母亲乳房的早期经验中,我们与母亲结合在一起。那时我们也与宇宙结合,与它结合,有了“与存在结合”的经验…… 这是人类存在的背景,暗含在伊甸园的每一个神话、每一个天堂的故事、每一个“黄金时代”——一种深深嵌入人类集体记忆的完美”(第283-284页)。在《爱与意志》(Love and Will)的兰克式结尾中,梅回到了他意识到和自我意识到自己在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双重存在时所感受到的敬畏、喜悦和恐惧:“我们意识的微观世界是已知宇宙的宏观世界。人能意识到自己和他的世界是可怕的快乐、祝福和诅咒”(第324页)。
梅在1972年出版的下一本书《权力与纯真:寻找暴力根源》延续了他对无力感的思考,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艾布扎格(2021)写道,“呼吁个人主义的、伪善的美国觉醒,认识到它自身的恶魔本质,它的善恶能力”(294页)。20世纪70年代中期,梅对“人类潜能运动”中普遍存在的反智主义迹象感到震惊,许多参与者吸收了他和他的同事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和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最富有的想法,把它们稀释成“我的十年”的自恋、EST等威权邪教组织、政客和汽车的广告活动、对新时代宗教的超个人尝试,以及裸体邂逅团体。“梅的批评,”艾布扎格指出,“针对的是20世纪70年代,在水门事件、越南战争、三里岛核灾难和伊朗绑架美国人质之后的陷入焦虑和疲惫漩涡的美国文化”,(第320页)。
罗洛的新文章、讲座和书籍定期出现,他继续他的惩罚式写作和演讲,包括一篇感人的致敬保罗·蒂利希,保卢斯:1973年的友谊回忆,创造力的赞歌,1975年的创造的勇气,1981年的自传体《自由与命运》,1985年的《我对美的追求》,以及1991年的《为神话呐喊》,这或许是他最关心的主题。1988年,结束了一段短暂而麻烦的第二次婚姻后,他与荣格主义治疗师乔治亚·李·约翰逊(Georgia Lee Johnson)再婚,这一次他很幸福。约翰逊“直觉地感觉到,罗洛厌倦了总是做一个伟大的人,同时又害怕放弃权威和控制的光环。他需要简单的人类的爱和关怀。她使他平静下来,他使她高兴”(第329页)。
“创造的勇气”
在1975年出版的也许是他最杰出的作品《创造的勇气》(The Courage to Create)一书中,梅再次强调了兰克原始存在焦虑的“两种恐惧”,这两种恐惧都必须面对,才能过上充满爱和创造力的生活:
第一种他称之为“生活恐惧”。这是对独立生活的恐惧,对被抛弃的恐惧,对依赖他人的需求。它表现在一个人需要把自己完全投入到一段关系中,以至于一个人已经没有自我来与之联系。事实上,一个人变成了他或她所爱的人的反映——这迟早会让他或她的伴侣感到厌烦。正如兰克所描述的,这是对自我实现的恐惧。生活在妇女解放前40年左右的兰克断言,这种恐惧在女性中最为典型。
兰克将另一种恐惧称之为“死亡恐惧”。这是对被对方完全吸收的恐惧,对失去自我和自主的恐惧,对被剥夺独立的恐惧。兰克说,这是男性最害怕的事情,因为一旦关系变得太亲密,他们就会打开后门,以免匆忙撤退。
事实上,如果兰克活到今天,他会同意,男人和女人都必须面对这两种确定的不同程度的恐惧。我们一生都在这两种恐惧之间摇摆。它们确实是等待着任何关心他人的人的恐惧。但是,如果我们要走向自我实现,就必须直面这两种恐惧,并意识到一个人不仅要通过做自己,还要通过参与他人的自我来成长。(第18-19页)
罗洛再一次为全人类说话,但也是自传性的,他自己与他吞噬性的母亲,马蒂,以及所有他爱过或没爱过的女人有关的恐惧。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胜利的《美国的早晨》(Morning In America),用怪诞的赞美诗歌颂“贪婪是好的”觉醒之后,人们有理由担心存在主义心理学的灵魂会随着罗洛·梅在1994年死去虽然仍有一些强有力的声音,尤其是罗洛的密友欧文·亚隆和詹姆斯·布根特的声音,但在20世纪80年代,推动这场运动的力量明显开始减弱。正如艾布扎格(2021)所观察到的那样,罗洛“敏锐地意识到,心理疗法在美国文化中曾经夸耀的地位,自1950年至1970年的宁静岁月以来,已经急剧下降”(第336页)。
“生命不息”
艾布扎格温柔地叙述了罗洛最后的岁月,揭示了罗洛在他们的对话中常常充满渴望地想知道他会给21世纪留下什么遗产。“人们还会读他的书,讨论他的思想多久?”谁会知道他的名字?”(第335页)。艾布扎格在一个名为《生命不息》的简短尾声中提出了这些深刻的问题,他引用了最近在互联网上的搜索——包括亚马逊和其他在线评论罗洛的书——作为证据,证明他的作品仍然被普通人广泛阅读,他们感到与他们自己和相互间的脱节,仍然被罗洛的灵魂考古学所吸引。
当我们在21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艰难前行时,人类一如既往地渴望在日常生活中体验爱、意志、勇气、创造力和超越。如今,在瘟疫肆虐的年代,脸书(Facebook)和社交媒体成了我们孤独的新图腾。我们被周围的混乱所迷惑,今天的我们无法理解隐藏在我们孤独之下的原始的存在焦虑,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促使罗洛写了《人类探索自己》的“空虚时代”一样。如果人类能在全球气候变化中幸存下来,历史学家无疑会将21世纪人类生活的头几十年描述为“孤独的时代”。2018年,甚至在瘟疫到来之前,英国就任命了世界上首位孤独大臣。2021年2月,在发生一系列自杀事件后,日本任命了第二名。
在完成对罗洛的生活和工作的叙述后,艾布扎格选择不去研究罗洛的遗产问题,而是将其作为心理学专业领域的研究对象。他正确地判断,这样的研究将需要一种不同的尾声,在心理学学术期刊上记录存在主义思想的变迁。艾布扎格认为他的目标是探索与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精神奥德赛紧密相连灵魂的泰坦(Titan)的生活和工作。
然而,有人想知道,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数据碎片来寻找线索,以更全面地描述罗洛的遗产? 除了网上关于罗洛对非专业人士的吸引力的广泛证据之外,我还在学术书籍和同行评比出版物中看到了有希望的迹象,这些迹象支持这样一种假设:至少罗洛的灵魂考古学词汇,如果不是他的诗歌风格和人文学习的深度,仍然吸引着21世纪的许多心理学家。正是积极心理学的老前辈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 2021),他过去一直在诋毁存在主义心理学的“不科学的模糊性”,现在正从事从古希腊开始的对历史上“意志、责任和选择”(第1页)的研究。然而,罗洛关于意志、责任和选择的著作,以及奥托·兰克的著作,都没有被塞利格曼引用,塞利格曼拒绝直面人类生存的苦难,尽管保罗·王(Paul Wong)英勇地努力培养“积极心理学2.0”。在积极心理学1.0的语言中,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很难找到“痛苦”、“绝望”或“死亡”这样的词。
无论“积极心理学1.0”的忠实拥趸们是否注意到这一点,建立存在心理学科学的前景正在改善。国际存在主义心理学科学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cience of Existential Psychology, 2021)在其网站上向罗洛·梅和奥托·兰克致敬,写道:“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正在使用不同的方法——从控制实验室实验到大数据集分析——来严格测试各种存在主义担忧的角色。”这一趋势几乎出现在当代心理科学的每一个领域,包括认知和神经科学、社会和人格心理学、临床和咨询心理学等等。越来越多的主流同行评议研究期刊,如《人格与社会心理学评论》(2010)、《宗教、大脑与行为》(2016)、《普通心理学评论》(2018)和《社会与临床心理学杂志》(2020),已经举办了专门关注存在主义心理学话题的‘专刊’。”
虽然罗洛不反对控制的实验室实验或大数据集的分析,但我相信,他会批评世界主要期刊特有的写作风格。他在《爱与意志》中警告说:“理性的语言只能讲述故事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停止使用散漫的语言,我们就会使自己贫瘠”(1969年5月,第137页)。不过,他可能会因为存在主义心理学不再被塞利格曼教授等人斥为“不科学”而感到高兴。他在《爱与意志》中警告说:“理性的语言只能讲述故事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停止使用散漫的语言,我们就会使自己贫瘠”(1969年5月,第137页)。不过,他可能会因为存在主义心理学不再被塞利格曼教授等人斥为“不科学”而感到高兴。
虽然罗洛的名字在今天并不为学术心理学家和他们的学生所熟知,但罗洛散文的文学品质仍然吸引着我们当中最敏感的心理学家。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斯科特·巴里·考夫曼的《超越:自我实现的新科学》(考夫曼,2020),虽然写这本书是为了庆祝亚伯拉罕·马斯洛在创造“存在”心理学方面的杰出贡献,但也高度赞扬了罗洛·梅。考夫曼是流行的“心理学播客”的主持人,他很高兴地把罗洛·梅视为自己的偶像之一。在重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时,考夫曼将过去四十年同行评比的心理学研究完美地编织在一起,就像一幅多彩的挂毯,展示了罗洛关于灵魂的考古学中的几乎每一个术语,即使考夫曼引用的研究人员在他们的因素分析中排除了“灵魂”这个词,几乎忘记了罗洛的名字,也无法接近他在艺术和人文学科中的学术深度。但伟大的思想家不会死,正如考夫曼启发人们重新想象马斯洛的生活和工作所表明的那样。真理是坚不可摧的。“归根结底,”考夫曼(Kaufman, 2020)写道,这句话会让梅和兰克都感到高兴,“美好地死去的最好方式就是好好地生活”(第238页)。
最近,另一个罗洛可能会钦佩的写作例子是,谢尔顿·所罗门(Sheldon Solomon)、杰夫·格林伯格(Jeff Greenberg)和汤姆·Pyszczynski (Solomon et al.,2015)的《核心的蠕虫:论死亡在生命中的作用》(The Worm at The Core: On The Role of Death in Life),他们以充满活力的语言回顾了25年来他们为检验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的论点而付出的爱的劳动,这一论点的灵感来自贝克尔对奥托·兰克的研究,即生与死的恐惧是理解人类为什么会做他们所做的事情的基础。贝克尔凭借《否认死亡》获得普利策非虚构文学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令人惊叹的散文风格,将克尔凯郭尔深沉的天才与兰克的天才结合在一起。贝克尔(1973)赞赏地指出:“罗洛·梅最近在《爱与意志》中对‘爱与死亡’的精彩讨论中,重新使用了兰克学派的视角。”(第289页)
1994年罗洛去世后,回顾美国职业心理学近30年来的发展,我大胆地推测,罗洛与柯克·施耐德(Kirk Schneider)合作的最后一本书《存在心理学:综合临床视角》(施耐德和梅, 1995)很可能被视为在主流心理学中为存在主义思想的重生埋下了种子。最初,罗洛是受麦格劳-希尔出版社委托,担任这本书的第一作者,但在他遭遇了中度中风后,他觉得自己不能再担任这个职务,于是请施耐德来担任第一作者。作为三年合作的产物,这本在罗洛死后出版的书回到了他在1958年的里程碑式著作《存在》中首次提出的“整合”视角,展示了许多思想和治疗领域,包括心理动力学、冥想、身体、家庭系统和认知-行为方法,可以在存在主义心理学的冠层下整合。“首先,”施耐德和梅(1995)宣称,“这是兰克存在的义务。他对基本生活结构、即时性和关系以及心理治疗的艺术性的强调已经成为当代存在主义实践的标准组成部分(第81页)。
就像双螺旋一样,存在主义的无意识把自己包裹在每个人的全部。“摇篮在深渊之上,”纳博科夫(1951)写道,“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只是两个永恒的黑暗之间短暂的一道光。虽然这两个人是同卵双胞胎,通常男性看待产前深渊的时候比他即将面对的深渊要平静得多(第1页)。
要想理解人类普遍的苦难,那不就是奇怪的生活意识吗?——模糊地意识到,我们短暂地活在一粒尘埃上,因为它毫无意义地围绕着太阳旋转,而太阳本身只是浩瀚而不可理解的宇宙空间中更大的一粒尘埃——这难道不是人类存在的唯一最重要的事实吗? 意识的本质仍然是完全神秘的。神经科学家们甚至无法对意识的定义达成一致,也无法对有意识的“自我”的定义达成一致,更不用说对两者进行测量了。我们无法解释,正如哲学家大卫·查默斯(David Chalmers)的名言所说,大脑的水是如何变成意识的酒的。没有任何科学仪器被发明来检测意识的存在或缺失。奥托·兰克所说的“生活的意识”在我看来与查尔默斯(Chalmers)提出的意识的“难题”是相同的,后者要求解释“我是”的第一人称体验是如何在宇宙中出现的。没人知道。意识仍然是一个谜中谜,笼罩在黑暗中,就像存在的无意识一样。也许,当我们谈到“科学”时,“存在主义的”这个形容词将不再是必要的时刻正在到来。
自从罗洛·梅去世后,科克·施耐德孜孜不厌地强调罗洛“综合”的观点内在的可能性,为美国和世界范围内更大的心理学界服务,并与塞利格曼等对罗洛的“非科学”工作持敌对态度的人展开了争论。在这一探索中,施耐德追随了他的导师的脚步,后者曾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卷入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他与意图阻止临床心理学家“无证行医”的弗洛伊德式的精神科医生展开了“大卫与歌利亚”之争。
著名心理治疗结果研究者Bruce Wampold(2008)在《心理评论》中回顾了施耐德的《存在-整合性心理治疗:实践核心指南》(施耐德, 2008),总结道其中阐述的整合原则可能“构成所有有效治疗的基础”(第6页)。这些原则很可能是心理治疗的“共同因素”(Wampold & Imel, 2015)。Wampold认为,重要的是治疗师本身,而不是他或她的理论取向。
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Shahar和Schiller(2016)断言,证实了Wampold的预期,“人文主义-存在主义运动不仅渗透到了临床心理学的堡垒,而且在总体上也渗透进了主流学术心理学,并采取了一种安静的,尽管坚定的控制”(第1页)。这是否意味着今天的主流学术心理学家充满了罗洛·梅对神话、诗歌、文学、音乐和艺术的狂热热爱? 他们知道奥托·兰克的名字吗?他们是否汲取了埃斯库罗斯、奥登、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菲茨杰拉德、歌德、卡夫卡、克尔凯郭尔、尼采、叔本华或华兹华斯的灵魂智慧?几乎没有。然而,罗洛去世后,他的文学和哲学遗产启发了他的学生Ed Mendelowitz(2008)关于性格心理的创作;路易斯·霍夫曼(2019)谈东西方存在主义视角之间的桥梁;斯蒂芬·戴蒙德(1996年)论“魔力”和柯克·施耐德(2009b)的敬畏。
但对于罗洛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定论,因为存在主义焦虑仍被称为“减毒精神病综合征”和“破坏性情绪失调障碍”。只要设计标准手册的普罗克鲁斯特理性统治着美国心理治疗的赚钱机器,奥托·兰克和罗洛·梅的存在主义潜意识就不会出现在保险公司的计费实践中。兰克(1941)在他的最后一本书《超越心理学》(Beyond Psychology)中说,“我们似乎都从存在的无意识中退缩”,这种退缩“导致对理性思维的过高估计,也就是说,某种能够平息恐惧的理解”(兰克,1941,第277页)。更深刻的是,兰克坚持认为,“仅仅看到存在无意识的重要性是不够的”,“并以理性的方式指出它!”相反地,我们有必要去实践它,而在每一个时代,似乎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代表了英雄类型——区别于创造性——因为最初的英雄是敢于超越他那个时代公认的‘心理’或意识形态的人”(第14页)。罗洛肯定会同意。
当我们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时,在美国,没有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像罗洛•梅那样才华横溢,她对《美国的心智与灵魂》(艾布扎格的传记标题很有灵感)的阐释能抓住整整一代人的情感基调。在罗洛·梅的一生中以及以后,他给他的学生、崇拜者和继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圣人,但他是美国心理学中最具创造力的人物之一,他带着尊严(通常也带着愤慨)推动了一种治疗观的兴起。艾布扎格观察到,正是这种治疗观引入了爱、勇气、责任、创造力等词汇,直到今天,许多美国人仍在使用这些词汇来谈论他们的心理和灵魂,他们的情感和精神生活。
作为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当之无愧的接班人,罗洛·梅是一位对于存在始末富有传奇色彩的探索者,一位慷慨的导师,一位深受爱戴的精神导师,一位杰出的散文文体家——一位美国大师。在《阿波罗的躯干》的最后一句中,里尔克敦促道:“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 从来就不是一个艺术家愿望落空的艺术大师,罗洛永远在运用他的创作意志的普罗米修斯力量,他的守护神,来重生和不断地重生自己。最后,这位“受伤的治疗师”以极大的勇气,敦促罗伯特·艾布扎格用明暗对比的所有阴影,完整地展示他那神一般的、受厄罗斯伤害的生活。当罗洛·梅在1936年遇到奥托·兰克时,他感觉到他遇到了自己的存在。 多亏了艾布扎格权威的传记,我们现在有幸目睹罗洛如何用他神圣而狂野的一生去达到,达到,总是达到,把他灵魂的结巴变成一件艺术作品。
参考文献(见原文)
作者介绍:罗伯特·克雷默(Robert Kramer)是匈牙利布达佩斯罗兰大学精神分析学教授。2015-2016年,他担任布达佩斯国立公共服务大学首任公共领导力国际主席,为抗议欧尔班政权的腐败而辞职。他是奥托·兰克《差异心理学》的编辑。《美国讲座》(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6年);与E.詹姆斯·利伯曼合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信件》和《奥托·兰克:精神分析的内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12年);著有《关系治疗的诞生:卡尔·罗杰斯遇见奥托·兰克》(心理社会出版社,2019年)。
译者简介:张文娟,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毕业,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原文出处:Kramer, R. (2022). Discovering the existential unconscious: Rollo May encounters Otto Rank.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37/hum0000272
需要原文或其他事宜可以联系作者邮箱:robertkramer@gwmail.gwu.edu
最新动态
- 发现存在的无意识: 罗洛·梅遇到奥托·兰克(一) null
- 发现存在的无意识: 罗洛·梅遇到奥托·兰克(二) null
- 发现存在的无意识: 罗洛·梅遇到奥托·兰克(三) null
- 心悸、心律失常与心理障碍 null
- 焦虑障碍药物治疗研究进展 null
- 焦虑症治疗药物和干预手段临床试验研究现状 null
- 儿童分离性焦虑障碍的认知行为治疗效果及影响因素 null
- 日语专业大学生听力焦虑与听力策略的调查研究 null
- 高中生人格特质、睡眠状况与焦虑的关系 null
- 礼仪教育对儿童社交焦虑的预防、疏导与塑造 n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