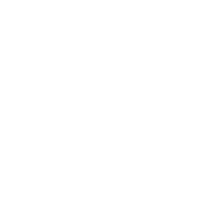发现存在的无意识: 罗洛·梅遇到奥托·兰克(一)
作者:罗伯特·克雷默(Robert Kramer ) 中文译者:张文娟
( 注:该论文公开发表得到了作者本人的同意,这也是该论文的中文版在中国大陆首次公开发表。)
译者导读:罗伯特·克雷默教授的这篇文章讲述了精神分析学派的奥托·兰克对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奠基人罗洛·梅带来的影响,尤其是促使梅对人的理解:发现存在的无意识。翻译的过程中,我感觉罗伯特·克雷默教授文笔精妙,读来让人心驰神往,似乎也回到那个年代那个地方,感受到两位心理治疗大师的对话一般。如果兰克代表了对弗洛伊德传统精神分析的背叛,那正是基于这种背叛,产生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苗头,从精神分析式的被动分析走向人本主义的自由意志。通过两位心理治疗大师的连接,我们似乎更清晰得看到精神分析与存在哲学的结合,并促使心理治疗从传统精神分析走向人本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历程。
罗洛·梅始终承认,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遇到奥托·兰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然而,直到现在,很少有学者了解兰克对罗洛的重要性。参考罗伯特·艾布扎格的梅的新传记
在本文中,我来讲一个完整的故事。
关键词:罗洛·梅,奥托·兰克,存在主义的无意识
“我被兰克学派的思想所感染”——卡尔•罗杰斯
“没有什么能代替阅读兰克。他有着多年的洞察力和思考”——厄内斯特·贝克尔
“当我读到他的作品,尤其是《意志疗法》时,我不禁大吃一惊” ——欧文·亚隆
他对生活有着巨大的欲望和对宇宙意义的强烈渴望,但他总是很虚弱,孤单和脆弱。81岁时,罗洛·梅对光明的消逝感到愤怒,他大声疾呼:“我没有时间去死”(艾布扎格,2021年,第332页)。1909年,梅出生在一个美国偏僻的中西部地区,他卒于1994年,享年85岁。作为20世纪下半叶美国最著名的心理咨询师和公共知识分子,他一生的热情都在努力缓解一出生就被扔进冷漠宇宙的人的焦虑。
梅(1969)在《爱与意志》中写道,“艺术家呈现了人类破碎的形象,但在行动中超越了它,将其转化为艺术...”作为一个总是感觉自己破碎的人来说,正如奥托·兰克所说,神经质的人是“艺术家愿望落空的艺术大师”,即不能将自己的冲突转化为艺术的艺术家”(23-24页)。在被兰克从她的写作障碍中解放出来后,阿娜伊斯·宁(Anaïs Nin,1966)观察到神经症是“生命中灵魂的口吃”(第295页)。
用一生的努力,将自己的破碎和“充满感情的结巴”变成一件艺术品的罗洛·梅(Rollo May,1975),在《创造的勇气》(The Courage to Create, 1975)一书中,提供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开创式的构想:“创造力是一种对不朽的渴望…… 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发展面对死亡的勇气。创造力来自于这种斗争——在这种反抗中,创造性行为诞生了……一种超越个体死亡而活的激情”(第31页)。我们生来为死。但我们也生来为活——去画画、唱歌、跳舞、写作、作曲、发明治疗疾病的方法,并想知道我们在浩瀚的、无法理解的宇宙中所处的位置。梅坚持认为,只有给予和接受真正的爱,并表达我们的“创造性意志”,兰克创造了这个术语,我们才有希望治愈,我们的破碎,痛苦和永恒的孤独,尽管治愈是暂时的。
“由内而外”
罗洛·梅始终承认,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遇到奥托·兰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然而,直到现在,很少有学者了解兰克对罗洛的重要性。参考罗伯特·艾布扎格的梅的新传记,在本文中,我来讲一个完整的故事。由同样的热烈披露和冷静分析组成,艾布扎格的最终评估将成为将黑暗悲剧性的兰克学派对于存在的无意识的认识带入了美国的墨守成规的反智的意识的,自称“受伤的治愈者”的永恒敬意。
罗洛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他是如何捕捉到整整一代美国人,一个从来没有以愿意仔细审视他们的“心灵和灵魂”,更不用说黑暗的暴力内心而闻名的物质主义的民族的“感觉的基调”呢?
为了解开这个问题,奥德雷和伯纳德·拉波波特犹太研究董事主席和德克萨斯大学历史与美国研究荣誉退休教授罗伯特·艾布扎格,花了30年时间研究罗洛的生活和著作。凭借专业历史学家的敏锐洞察力,艾布扎格挖掘了梅几十年来的日记、信件、梦境分析、手稿和布道辞,并与梅和他的几十位同事、朋友、情人和学生进行了广泛的口头采访。罗洛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他全权委托艾布扎格引用他当时日记中记录的所有思想和情感,甚至——也许尤其是——最糟糕的、自我伤害的那些。”这种亲密的优势,艾布扎格断言(2021),“让我能够从内到外写梅”(第十六页)。阅读艾布扎格引人入胜的传记,其中充满了从梅半个世纪的日记中摘取的剥皮般严厉批评的段落,就像偷听罗洛坐在心理分析师的沙发上倾诉衷肠。
艾布扎格将心理学大师的混乱生活与20世纪中期美国动荡的政治、文化和知识氛围无缝地融合在一起。艾布扎格用一句话总结了他的论点:“当被视为现代美国文化中心戏剧的一部分——自由主义新教作为文化仲裁者的衰落与改变了许多美国人理解生活中情感和精神问题的方式的“治疗”视野的同时兴起。梅的生活具有更大的意义。(第12-15页)”
从梅的第一本书《心理咨询的艺术》(1939年)开始,艾布扎格的书的标志之一就是使用伪装成第三人称案例历史,“毫不掩饰地讲述了他自己的生活”(第117页),以及“当他将哲学、宗教和心理学融合在一起时,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广泛的、有时令人眼花缭乱的综合”(第122页)。以诗人对语言的细腻敏感,梅“成功地将自己近乎强迫性地讲述和复述自己的人生故事,转变为对人类境况不断演变的诠释”(第111页)。
“我不好,因为我来自她”
1909年,罗洛·梅出生在俄亥俄州,母亲玛蒂情绪不佳,父亲Earl Tuttle May,风流成性,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区域秘书,在罗洛出生的前一天,他失踪了,几天后又回来了。“马蒂,”艾布扎格写道,“确信他当时和情人在一起”(第5页)。罗洛的母亲把罗洛暴躁、滥交的姐姐露丝(Ruth)流产的胎儿保存在一个罐子里,“当她被激怒时,就会把它拿出来,威胁地朝Earl Tuttle和孩子们挥舞”(第69页)。 在他们的余生中,罗洛和露丝一直是折磨而痛苦的关系。
早年时,作为马蒂的第一个儿子,“罗洛成为她爱和愤怒的亲密对象,她对Earl Tuttle的外遇的绝望和怀疑让这个孩子负担沉重。”70多岁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母亲需要我——父亲与其他女人厮混——她把我抱在怀里——我拥有她的乳汁,爱抚着她。”她常常被证明是不可预测的而精神错乱,前一分钟在依偎,后一分钟就朝他尖叫”(第6页)。在罗洛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马蒂,除了接近生命尽头的时候,仍然对她的儿子充满了虐待和排斥,“贬低他的成功”,充当“他想象和现实中消极的、批判的灵魂”(第276页)。
1949年父亲去世后,罗洛拒绝参加葬礼。马蒂于1974年去世,享年90岁。与父亲不同,罗洛总是在经济上和情感上支持她,但一想起她就会颤抖。在1970年的一篇紧张的日记中,61岁的罗洛在日记中为继承了母亲受损的灵魂而感到痛苦:“我不好,因为我继承了她的灵魂,”他对自己情感上和性上都被吞没的母亲感到哀悼,“我带着污点。我得道歉……我背负着她的重担”(第276页)。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罗洛在日记中使用人称代词“(I)我”时,他经常会省略“am(英语中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这个词——这也许是他对出生在这样一个不幸的家庭中是否能真正“做自己”的永恒怀疑的忏悔。这也可能是为什么他后来如此热情地将“我是我的体验”作为一种完全活着的感觉的核心。
20世纪20年代,罗洛在奥柏林学院读本科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哦,我可以加入隐形合唱团》(Oh May I Join the Choir Invisible,第22页)是他最喜欢的诗歌之一,也是他一生的最爱。前三行诗完美地表达了他渴望永生的梦想,即使是在他年轻的时候:
哦,我可以加入隐形合唱团吗
那些不朽的死者会重生
他们的存在使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好
“超越上帝的上帝”
1930年从欧柏林大学毕业后,罗洛在希腊任教三年,每天接触希腊挑战时间的神话、古典建筑、古代戏剧和人文哲学,令罗洛感到兴奋。在他20多岁的时候,他开始经历“一种深深的渴望,一种强烈想要在宇宙中找到自己的家的渴望”(第18页)——一种对宇宙意义的渴望,这种渴望从未离开过他。
从一开始,罗洛·梅就努力去发现他“自己的天赋”,他感觉到,他的天才与“我们心中的上帝”是相同的(第39页)。于是,梅开始不知疲倦地将自己神话化,以普罗米修斯和其他泰坦巨神的形象重塑自己。“只有创造的过程,”艾布扎格说,“允许一个人与自己神圣的部分交谈”(第42页)。正是在这种“创造的勇气”中,罗洛·梅最终找到了他对生活的“热情”,他独特的艺术天赋——古希腊人称之为en-theos-mos是“内在的上帝”。
1932年,梅还住在希腊时,在维也纳与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一起参加了一个为期一周的研讨会。阿德勒关于童年“自卑情结”的理论和孩子们试图从自卑中解放自己的“指导性小说”(或优越感的神话),与罗洛自己的自我怀疑和不断努力挖掘的自己内在上帝相对应。
1933年,“始终关注自我神圣”的梅计划从事基督教牧师的职业 (第111页),进入纽约的联合神学院,但父母离婚后他回家照顾弟弟妹妹,他的研究被打断了两年。1936年至1937年期间,罗洛与比他年长23岁的德国神学家保罗·蒂里希(Paul Tillich)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作为一个终生的导师,蒂里希把这个天真的中西部人介绍给了一群才华横溢、有争议的纽约欧洲人émigrés,其中包括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库尔特·戈德斯坦、欧内斯特·沙赫特尔、赫伯特·马尔库塞、埃里希·弗罗姆和他的妻子弗里达·弗罗姆-瑞克曼。作为联合大学的一名学生,罗洛被蒂里希的“超越上帝的上帝”——超越有神论的上帝——作为“存在的基础”的构想迷住了。
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女性诱惑者,蒂里希享受着与他有时不情愿的妻子汉娜的开放式婚姻。他向梅和他的妻子弗洛伦斯介绍了“在这座城市的艺术和知识社会中,性实验是地方性的,但在神学院里,许多人对此感到厌恶”(第101-102页)。在他的余生中,罗洛被希腊神厄洛斯的箭射伤,他不顾自己或她们的婚姻状况,寻找无数的女人来满足他的性欲。但是,正如罗洛的日记所揭示的那样,在他的多次性接触中,他仍然无法完全从他早期与抑郁和愤怒的母亲马蒂经历的可怕的性和情感吞噬中解脱出来。
“弗洛伊德圈子里未被承认的伟大天才……”
1936年,梅阅读了奥托·兰克的存在主义著作。他发现,这位叛逆的弗洛伊德主义者比弗洛伊德和阿德勒更令人信服,因为兰克强调个人的独特性,强调寻求解放个人精神和创造潜能的疗法。”受兰克的启发,”艾布扎格写道,“梅在日记中创造了一个新的流行语:‘勇敢地、充分地活在当下,就是把自己从过去中解放出来’”(第80-81页)。
兰克认为神经症是一种创造性的成就,而不是弗洛伊德所坚持的一种疾病,罗洛被这一观点所迷惑,在日记中宣称:“我是神经症!”艾布扎格引用日记中的话补充说:“这是‘对某种奇特生活的客观评论,这个奇怪的人就是我’,这是真正创造力的关键。”伟大的艺术和任何领域的艺术触觉都是在克服神经症的斗争中锻造出来的。没有神经症,就没有艺术”(第84页)。这种观点在精神分析学中是闻所未闻的,它把艺术归结为幼稚欲望的升华。 对弗洛伊德来说,所有人类的经验,所有的思考和感觉,所有的文化和艺术,都只是性冲动的伪装衍生物。但是,兰克坚持认为,弗洛伊德无法解释为什么人类共有的生物动力产生的不是性,而是艺术创作。作为一个生物过程,性只能导致物种的繁殖,而不是文化或艺术的生产,这需要一个有意识的有感情的人去创造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的、在自然中不存在的东西。
1937年,28岁的罗洛为了帮助自己做出结婚的决定,接受了哈里·伯恩(Harry Bone)的治疗,后者是一名在巴黎接受兰克培训的精神分析学家。“他对兰克的神经症理论有了更多的了解,兰克认为神经症抑制了创造力,他强调治疗过程中‘此时此地’的对话——所有这些都成为了梅成熟的治疗方法的关键方面”(第88页)。六十年后,梅为《差异心理学》(1996年出版)撰写了序言,这本书收集了兰克从1924年到1938年在包括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在内的美国各所大学所做的22场演讲:“我一直认为奥托·兰克是弗洛伊德圈子里未被承认的伟大天才,”梅(1996)在他的前言中证实,这是他名字下的最后一篇文章(第14页)。罗洛在去世前不久说:“兰克比他的时代早了几十年,他说神经症是创造力的失败,是人类想成为艺术家而未能如愿的痛苦,一个失败的艺术家。在这些讲座中,兰克用简单的英语探索了我与你、分离与结合、意志与爱、创造力与罪责之间的丰富互动。”罗洛把兰克的美国演讲称为“令人眼花缭乱”(第12页)。
参考文献(见原文)
作者介绍:罗伯特·克雷默(Robert Kramer)是匈牙利布达佩斯罗兰大学精神分析学教授。2015-2016年,他担任布达佩斯国立公共服务大学首任公共领导力国际主席,为抗议欧尔班政权的腐败而辞职。他是奥托·兰克《差异心理学》的编辑。《美国讲座》(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6年);与E.詹姆斯·利伯曼合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信件》和《奥托·兰克:精神分析的内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12年);著有《关系治疗的诞生:卡尔·罗杰斯遇见奥托·兰克》(心理社会出版社,2019年)。
译者简介:张文娟,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毕业,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原文出处:Kramer, R. (2022). Discovering the existential unconscious: Rollo May encounters Otto Rank.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37/hum0000272
需要原文或其他事宜可以联系作者邮箱:robertkramer@gwmail.gwu.edu
最新动态
- 发现存在的无意识: 罗洛·梅遇到奥托·兰克(一) null
- 发现存在的无意识: 罗洛·梅遇到奥托·兰克(二) null
- 发现存在的无意识: 罗洛·梅遇到奥托·兰克(三) null
- 心悸、心律失常与心理障碍 null
- 焦虑障碍药物治疗研究进展 null
- 焦虑症治疗药物和干预手段临床试验研究现状 null
- 儿童分离性焦虑障碍的认知行为治疗效果及影响因素 null
- 日语专业大学生听力焦虑与听力策略的调查研究 null
- 高中生人格特质、睡眠状况与焦虑的关系 null
- 礼仪教育对儿童社交焦虑的预防、疏导与塑造 null